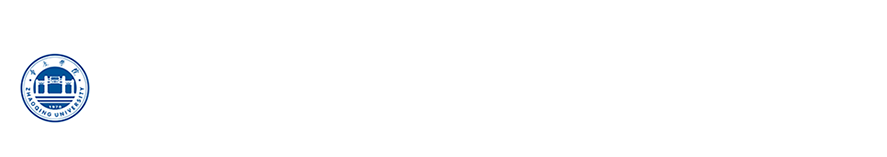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代表作品有《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2022)等多部著作。
我唯一一次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县,是在20年前的春天。那时,当地正在开发旅游,上游建设拦水坝,河道水浅,无法乘船前往老司城,只好走山路。由于那条路已好久没人走过,即便有向导带路,也需要用砍刀不时劈砍密布的杂草林木,才能通行。有时路过崖边的窄径,同行者要手拉手而过,若不小心翼翼,便有坠下的危险。
经数小时的跋涉,大约下午3时,终于赶到老司城,当地迎接我们的人大概也一直饿着肚子,于是赶紧招呼我们先去吃饭。这时有位本地文化人走在身旁,问说这里有块墓碑,但墓主去世时间的纪年不明其意,出生则是在明代天启年间。我问是什么年号,答曰“大周”。我一听,这不是吴三桂的国号吧?便顾不得吃饭,立刻请他带我去看。

位于永顺老司城的墓碑
那个地方距离我们吃饭的地方只有几百米,当时阳光灿烂,周围是小块的稻田,一对夫妇还在田里忙着。坡上的杂草间有块不起眼的小碑,一米多高,不知道是否一直就在这里。碑上正中的文字是“诰封正一品命服太夫人显妣□□□□”,右边是“生于明天启癸亥年十月十四日甲□□”,左边是“殁于周丁巳年三月二十四日辛□□”,最后的落款是“周四年岁次丁巳仲冬月初三日孝□□□”。
即便是在大学里读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也未必知道这个“周”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在明朝倒数第二个皇帝的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周”。此“周”是吴三桂在“三藩之乱”末期建立的国号,明天启癸亥年即明天启三年(1623),周丁巳年即清康熙十六年(1677),也即周四年,因为吴三桂在康熙十三年(1674)就称周王元年,尚未称帝,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才定国号为大周,改元昭武。在大多数历史书中,吴三桂被视为反复无常的小人,他的政权标识不为人所知,也是颇为正常的事。
小小墓碑,寥寥数字,让我十分兴奋,回到饭桌上便迫不及待地向大家述说我的发现:第一,时在清康熙年间,但墓碑的纪年却用了吴三桂“三藩之乱”时的政权纪年,说明墓主这家人是接受了吴三桂政权为正统的;第二,墓主的一品诰命夫人自然就是吴周政权封的;第三,这提示我们,西南地区、特别是山区的土司系统往往与朝廷具有复杂的关系,这种疏离的关系也是有很长的传统,所以这块“附逆者”的墓碑从清代至今一直没被捣毁,是需要对西南地区的生态关系、族群关系及其与王朝关系深入研究才能给予解释的。此后,我经常在课堂上提到这个可以从一块墓碑看到大历史的例子,也写文章讨论过那个“不清不明”但又“无明不清”的时代。
在近半个世纪前我走上学习历史之路的时候,从未想过我会确信无疑地说,如果哪一天我无法在山河间跋涉、在街巷里穿梭、与操着不同语音的人们一起聊天,我的学术之路就会终止。也从未想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居然不只是一句励志的口号,而是践行始终的治学方法。在田野中时有所见所闻,向我提出新的问题,甚至引发新的研究领域,而不似传统的历史研究者,他们虽然也会实地考察文物古迹,但大多只是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后的增广阅历而已。
20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到晋东南的阳城,是因为清康熙时期的大学士陈廷敬故里在那里。皇城村的张书记是个有魄力的人,因为村里开小煤窑致了富,就想到把皇城相府开发成旅游点。他通过山西籍的首都师范大学阎守诚教授邀请了一批学者开了一个讨论会,为其出谋划策,事后给学者们发劳务费,看似厚厚的一袋,打开一看,都是一元钱一张的、又旧又脏的票子,知道这都是村民劳动所得的血汗钱。
那次到阳城只能算是匆匆一瞥,但也足以让我知道晋东南是一个尚待发掘的宝藏,只是对其体量的认识,还只是九牛一毛。数年后,我与学生几次到晋城地区调研,还先后在这里组织了两次田野研习营,仍然是“日日新,又日新”。
后来,学界戏称我们的调查是“进村找庙,进庙读碑”,原因是在乡村社会中,庙宇、祠堂(家庙)是聚落的中心,碑刻就是乡村公共生活的记录。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科大卫教授把庙宇比作乡村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我们第一次到晋城府城村的玉皇庙,原来只计划看半天,结果不仅发现庙中存有自北宋以来的碑刻数十通,而且有许多老人在庙中闲谈。在碑刻中,我们看到宋元时期的乡、管系统之下,有许多社的组织,而对于这个社会基层的组织系统,当时还没有什么研究。在明清时期的碑刻中,有了“七社十八村”的说法,这些社和村的名字也被一一列出,我们便去询问庙里的老人,这些村现在还在不在,村里还有没有庙?老人们说有啊!我和学生相视苦笑,这哪里是半天看得完的?要一个个村跑啊!

2005年10月,本文作者(左)在山西省陵川县的“太行第一文庙”
那个时候既不会驾车,也没有导航,更没有搜索引擎,只是找人介绍一个司机带我们在各村找庙。远远地看到有几棵高高的松柏,估计那里必有庙了,便让司机朝那个方向开,一般没有错过。只要庙里有老乡,就会问附近还有什么庙,就这样到了一处再找下一处,完全没可能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而且在晋东南,很少有进了庙后发现没有碑的。有的庙多年无人料理,殿宇摇摇欲坠,院中杂草丛生,但还是会有几通碑刻或立或仆,凄凉地守在那里。
这些就是被人们遗忘的历史。我们读过碑,拍过照,听过村民讲故事,或许在很多学者看来平淡无奇,但那正是多数人生活的常态。有一年正值深秋,手冻得冰凉,傍晚我们从一个村庙里走出来,四外静谧无人,夕阳之下,一片红彤彤的。此般情景,应该是跨越时空的。
历史学者,即便是共享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的历史学者,通常也不会像人类学者那样,在自己的田野点生活数月乃至数年,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当下的社会。有的学者主要是通过保存至今的历史档案来重建一个村庄或小城的历史,比如法国历史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罗芒狂欢节》。在中国,因为在乡村中留存的大量民间文献,学者们在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同时,又必须身临其境,结合当地人的口述和自身的观察,才能理解这些文献。尽管如此,历史学者在田野中也会发现许多文献中很难察觉的历史线索。
广东省新兴县是个不太出名的地方,不过在南朝梁时便有这个县名,又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圆寂之地。2018年3月,我们参观了慧能故居国恩寺后,曾问一位妇女,附近还有没有别的庙,她的回答是除了这个寺便没有庙了。我们将信将疑地驱车前行,行至一片农田旁,我忽然看到田边的山脚下有几间小屋,疑似庙宇,立刻停车。穿过农田一看,果然是两间后建的小庙,前有一大石及一亭,石边有三个大香炉,表明一直有人在这里祭拜。
根据门楣上的石匾,一座庙叫拆石寺,另一座叫水口寺,大门锁闭。拆石寺门旁的对联写道:“水源长流归宝地,口口声声论神文”;水口寺的对联是:“天天日日谈神灵,后桑揄组(榆祖)诵圣地。”书法和联文不甚讲究,还有错字,但这恰恰说明这出自普通百姓之手。最重要的是两副对联的字头构成“水口天后”,一下子让我们兴奋起来,趴在门缝往里看,果然拆石寺中供奉的是土地公和土地婆,水口寺里是天后。

2018年3月,广东省新兴县的村边小庙
新兴县位于佛山以西约110公里,又在晚明平定“傜(瑶)乱”后设立的罗定州以东约100公里,处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与当年傜(瑶)族聚居的山区之间,是个浅山丘陵地带。这两个不经意“发现”的小庙透露出的信息,可能告诉我们这里发生的从古代到近世的变化。庙前的大石应该是上古时期的社的遗存,古代的社可能是石头,也可能是大树,这种形态在华南、西南,乃至湖南、江西等长江中游地区仍多处可见,而且一直活在乡民的生活中。后来,人们慢慢地建庙祭祀,有的社变成了土地,也塑了神像。拆石寺大概就是社的变型。水口是南方乡村的重要景观,指村中河流的入口,往往也是村口,为了抵御顺水而来的阴邪之气,人们便在水口建庙以镇之。这里的水口庙以天后为神,说明沿海地区的神祇传入腹地,而背后则是晚明以降全球性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人流与物流互通,毕竟新兴西边的漠阳江直通沿海的阳江,距离晚明时期“海盗”活动频繁的上、下川岛不远。
回想起那位妇女的回答,或是因为她觉得除了国恩寺以外,其他都算不上是“庙”;或是因为她觉得,我们这些外来的“游客”不会对那些山野小庙感兴趣,不会到那里去烧香、捐钱,所以才有意这样对我们说。其实,正是因为“我者”与“他者”有意无意形成的共谋,才导致许多历史在文人的笔下消失不见。
2001年春天,我第一次去黔东南清水江边的锦屏县,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先到桂林集中,乘一辆面包车前往锦屏,车大约开了10小时。山路颠簸,我坐在最后一排,常被颠得跳起来,头碰到车顶。夜幕降临赶到锦屏县城,次日一早乘船,途经那块今已消失于水下的“奕世永遵”摩崖,在一个江湾的码头边登岸。一行在前来迎接的苗族妇女的歌声中爬山前往文斗寨,开始了首次清水江考察之旅。考察中遇到下雨,山路泥泞,有的学者脚一滑,就坐了“滑梯”,浑身斑驳。夜里被安排在寨子里的村民家住宿,第一次住在干栏式建筑里,四面的窗直接露天,看得见夜空中的星星。
当时,我们是在文斗的上寨和下寨等村进行考察,特别是去了解许多侗族和苗族村民家中山林契约文书保存的情况。20年间,清水江流域数以万计的明清契约文书得到搜集、整理和出版,而且有许多学者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撰写了多部著作和大量论文,使这个黔东南大山中少为人知的县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之地。
20年后,我又和几位朋友来到锦屏县的侗寨瑶白村,参加这里的村落仪式摆古节,而且是三年一度的“大摆”,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所谓“摆古”,即村寨仪式中由寨老讲唱村寨的历史,可知语言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传承尤为重要。历史学者如果只读传世文献,就会将人民的历史付诸阙如。
在摆古辞中,唱得最为详细的内容,是关于瑶白的10多个姓氏因为曾经被统一为滚姓,与周边其他村寨的通婚变得极为困难,后来不得不恢复各自原来的姓氏,可见这是他们需要不断重申的重要内容。这件被称为“破姓开亲”(即恢复本姓,从而可与邻寨结亲)的大事,发生在清雍正年间。据学者的研究,摆古辞中所唱的寨中各姓改姓为滚,是为了从原住民滚姓那里获得定居和开发的权利。立于瑶白和彦洞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婚俗改革碑》禁革舅家索要姑家(男方向女方索要)礼银的习俗,是上述变化的延续,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村寨联盟的一种姻契关系表达。
这样的“婚俗改革碑”(这是今人的定名)在锦屏县并不只在上述两寨存在,在文斗、边沙,以及黎平、天柱、临近锦屏的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锹里等村寨中都有,年代自乾隆至光绪不同,且均为官府告示刻碑。从口头记忆的“破姓开亲”到文字书写的碑刻,固然反映了本地“文字下乡”和“礼下庶人”的变化,但在“婚俗改革”这种“文化语言”的背后,还可能反映了清代主家(原住民)与客家(晚来移民)之间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改变。

2021年7月,贵州省锦屏县瑶白村的摆古节仪式,右侧是寨子里的古碑
行走四方的历史学者不像人类学者那样长期在一地参与观察,将学习当地语言当作第一课,所以我们在田野过程中会遇到方言的问题。如果是在北方,问题还不太大,大体上是语调和习惯用法的差异,但在一些南方地区就会有交流上的不便。即便自秦朝以来就是“书同文”,但民间文献中时而会出现用汉字书写地方方言的情况,虽认识那些字,却不明其意。
前几年,我在太湖边的东山镇作水上人历史的研究。2019年春节刘猛将“出会”期间,我到东山的一个猛将堂去,里面有两间殿,没有牌匾。一间供奉的神像白脸持剑,肯定是刘猛将;另一间供奉的神像红袍长须,头上戴着有两根帽翅的官帽,不知是谁。我问院中的妇女,答曰“lāo niā”,无论如何也听不懂。这时正好有一些人进庙烧香,头上和腰上都系着白带子,应该是家里有丧事。我一下明白了,这个“lāo niā”应该是“老爷”,就是城隍。很多地方把城隍老爷简称为老爷,就像山西人说到老爷就特指关帝一样。后来才知道,东山共有7个城隍,这是其中之一。
太湖、鄱阳湖、洞庭湖都是中国的著名湖区,历史上还有很多的湖区水面渐渐缩小,比如山东的巨野泽到宋元时期便缩减大半,许多原来以水为生的人也渐变为种地的农民。关于水上人及其社会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用,但如果任其被人们遗忘,却有负历史学者的使命。其实对山区、草原的人群和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更需要历史学者跋山涉水,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启示,再去各类资料中努力寻找他们的蛛丝马迹。
也是在这次春节期间的调查中,才知道苏州市东山镇在农历六月有去太湖边的葑山寺抬猛将的习俗。当我听到人们是坐船去抬猛将的时候,心中一动:刘猛将本来是不是水上人的神灵?于是,当年7月就专门来看这次仪式。大约凌晨3点半,当地的朋友把我带到东山的一条港边的猛将堂,那里已经有几位妇女在作准备了。将近5点时,有个人在电喇叭中招呼村里的人来集合,随后女性在庙前两旁列队打鼓,一些男子便进庙作仪式后将猛将神像起驾,抬上停在港边的船。我上了安放神像的船,站在神像身后录像,看到各村猛将会的船队从各条港中划出,依次排列成队,向太湖进发。途中有前来敬神拜祭的,某一神船在水中转了三圈,然后继续前行,最后到达葑山寺举行仪式。

2019年7月,苏州市东山镇高田村前门头猛将堂外
这次参与观察启发了我关于刘猛将信仰与水上人关系的假设,并且确定了从刘猛将信仰作为切入点、以水上人上岸定居的历史来改写以往的江南史。后来,我又在庙港渔民演唱的《刘官宝》和江南普遍流传的《猛将宝卷》中知道了刘猛将小时被后母推到水里淹死、变为浮尸的情节,联系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国台湾沿海地区听到的浮尸被水上人奉为神灵的故事,以及水上人的赘婿习俗导致我对东山族谱中关于赘婿的大量记述的重新解读,都进一步丰富了我对于太湖水上人上岸历史的假设。

2019年7月,清晨前往葑山寺的船队
历史学者总以回答“何以中国”的问题为己任。有人以中原地区大型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来展现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系列纪录片用各地出土的文物讲述自先秦至秦汉的多元一体进程。但“何以中国”并不只是一个起源问题,因为中国是自古以来被不断构造的;中国也不是由某个地方、某个人群构造的,而是由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群共同构造的。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和事,都是回答“何以中国”的一部分。
带着这样的问题,30年里,我不仅在人类学者较少用力的长城和大运河沿线的城乡行走,也在费孝通先生特别关注的南岭、藏彝、西北三条民族走廊上寻寻觅觅。前者是国家主导的人工营造,后者曾是由自然条件保护起来的非汉族群聚居区,我把这两条人工营造的通道和三条民族走廊称为中国的“两带两路”。北边是长城带和西北走廊,南边是南岭走廊,东面是大运河,西面是藏彝走廊,这“两横两纵”构成一个井字形,构造了中国的基本骨架。我的希望是了解中国的血肉是如何一点点地附着在这“骨架”上的。
不要以为人们对长城和大运河都很了解。我从2003年起4次去过河北蔚县,调查过长城脚下的几十个堡寨,这几年又在甘肃、青海地区跑过4次,在大运河山东段和江苏段作过关于卫所和清真寺的调查,也只能说了解了一点皮毛,连文章都不敢写,对南岭走廊和藏彝走廊的认识就更谈不上了。
我第一次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因为学生要利用冕宁县档案馆里的清代档案做博士论文,也知道西昌是明代四川行都司及建昌卫的所在地,听说西昌还保留着明代卫城的城门和部分城墙。因为人生地不熟,所以麻烦老家在凉山的师妹介绍,安排了旅馆。在蓝天白云之下,我们不仅读到上百通的碑刻,也看到祠堂、族谱、墓碑。通过这些材料,可知在这个地区几乎所有城市和坝子的乡村,卫所制度带来的变化是极大的,因为当年这里的主要城市都是卫城或所城,而且占据了沿安宁河谷一线具有肥沃土地的坝子,少数回族村落分布在坝子边缘靠山麓的地方,而彝族则居住在海拔更高的山上。
正因为这样的体验,我们带着“卫所遗产在边疆”的问题,随后在河北蔚县、浙江温州、四川凉山和甘南川西北地区组织了4次团队考察,从而于2010年11月第二次来到凉山。这次除了重访西昌和冕宁坝子之外,还去了明代会川卫所在的会理。会理在凉山的最南端,隔金沙江与云南省的禄劝、元谋、武定三县相望,是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当年曾有银矿,到清代则是重要的滇铜产地。这里也保存着当年的卫城,从东、西、北关、北城门和钟鼓楼的位置,还可以辨识当年卫城的范围和十字街格局。北门即望帝门,一说是纪念传说中的蜀帝杜宇,另一说是北望帝都的意思,考虑到会理是处在当年彝族聚居之地,据守不易,应该是第二个说法的意思。不过,在这里看到的碑刻、族谱和契约文书大多是清代遗留下来的,从中看到的是汉族在这里定居、开发的历史。
第三次到凉山是在2023年火把节期间,我们从北边的甘洛一路向南,到越西、冕宁、西昌、会理,最后掉头北返,到了德昌。德昌在明代是个千户所,这里有座规模很大的仓圣宫,拜造字的仓颉。我发现,在西昌以北各县,像文昌宫、仓圣宫、魁星阁这样代表崇尚文教的庙宇不如西昌以南地区多,说明清时期汉族向南移民的规模比较大,而北边海拔较高的大小凉山地区主要还是彝族聚居区。
德昌县仓圣宫有块清咸丰五年(1855)的《募化至圣殿功德序》碑,根据碑上所述,乾隆时期这个地方大概学校很少,有位姓薛的先生就在川主庙里“设帐”教书,为表礼敬,就立了个仓圣的神牌。到了道光年间修了仓圣宫,一位王先生就把这个圣牌移送到仓圣宫。咸丰二年(1852)仓颉生日的时候,大家觉得仓圣宫“有前楹而无后殿”,圣牌放在仓颉像前也不合适,就决定修建后殿来置放圣牌。捐款者由知县带头,题名中有本地的各个寺庙,还有万寿宫(江西会馆)、禹王宫(湖广会馆)、南华宫(广东会馆)、赣南宫(客家会馆)、天上宫(福建盐业会馆)、桓侯宫(屠宰业会馆)等会馆,萧祠、陈祠、朱祠、胡祠、钟祠等家族都列名其上,可见当时这里是一个以商人势力为主导的移民社会,到19世纪中叶,各种力量在联合推动地方的教化。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大殿的左侧挂着一幅画像,前面摆放着三座小神像,中坐者官帽官服,两旁显然是土地公婆,也许中坐者是城隍。后面的画像中最上面摇羽扇的白发老者不知何人,应该是地位最高的神祇;左边持弓和叉者可能是彝族史诗中的射日英雄支格阿鲁;右边捧羊头的有可能是毕摩,但更可能是梅山教张五郎之类的传说人物。我询问仓圣宫中一位非常热情的女士,她也说不清楚。
最重要的是最上端的“三洞梅山”四字,说明这是梅山教的神图。梅山教本是在湖南苗瑶山区的狩猎人群中信奉的巫教传统,北宋开辟梅山之后,向广西等地传播,在此过程中受到道教正一派的影响,所以最上端的老者可能是张天师,甚至可能就是太上老君。我之所以觉得兴奋,是因为学术界通常认为梅山教是沿南岭走廊传播的,但此图证明梅山教也进入了藏彝走廊,这就揭示了南岭走廊与藏彝走廊各族群之间的互动。
历史学者不可能在当下的生活中重新经历一遍古人的生活,即便是人类学者终其一生可以经历此地或若干地方,体会当地人的部分时间段的生活,也无法经历所有人的全部。但历史与当下毕竟是有联系的,就好像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祖先的墓,虽然连祖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但因为知道那个墓里的人与自己有着切割不断的关系,就想努力去了解那个人的事,哪怕知道一点也好。
元代范梈的诗《王氏能远楼》中说:“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 后半句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每次走出一小步,逐步积累,终能看到广阔的天地。我庆幸能在全国各地游走,不知道走了多少步,也不知是否得以一窥寥廓江山,但终归不再是坐井观天。
2024年,我跟随朋友去了云南省哀牢山区,接着又去了四川省大巴山区。每到一处,都会看到和听到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情,产生许多从未想到的想法,有了许多与学术界同行对话的可能。无论是熙熙攘攘的西南坝子,还是大山中相隔遥远的散村,抑或是西北充满砂砾、唯见车辆疾驶而过的荒漠,闭上眼睛,好像历史上在这里生活的人群正从眼前蹒跚走过。
他们就是中国的血肉。